对于网上露营、野餐、骑行只要呆在家里,任何地方都可以去。和suv运输桨板这样的题,大家的关注度都很高,小编为你整理了知识点。
在这个单调的春天和初夏
受疫情影响,旅行和晚宴暂时取消。
去乡村,去户外,做一个城里人
身心的最终归宿
一条名叫温榆河的河流流经北京朝阳区和顺义区。两年来,河岸铺设了草坪、绿地,环境得到改善。今年春天以来,每逢周末和节假日,儒原江两岸绵延数公里的帐篷如雨后春笋般搭建起来。市民自愿允许老人、儿童和狗在河边度假。河边开满了紫色的二月兰花,即将进港的飞机低空飞行,倒映在河水中。大扫除期间,家住北京的歌手王晓坤向杜音热情推荐这个地方,他说“别再去人多的地方了,把车停在路边就行。”捧着空气,“好舒服,好舒服……”
东三环的亮马河已成为北京的塞纳河,吸引着半个城市的年轻人,东五环外的豫园河已成为北京的上野公园,成为家庭聚会的场所。
5月,随着北京餐厅暂时取消堂食,更多人来到河边野餐。许多人甚至不带帐篷,只是用天篷遮荫整个下午。比较淳朴的人们在河边的路上搭起简易的炉灶烧烤,或者坐在野餐垫上吃熟食。当精致露营、风情露营、野奢露营在各个城市盛行时,文威河的露营野餐却并不精致、时尚、奢华,只有一丝“野”字。这里主流的帐篷是迪卡侬包子形状的快开遮阳篷,每个售价300到400元。烧烤架生锈了,没有人拿着相机拍漂亮的照片,也没有人用手机直播。人们聚集在河边,因为他们无处可去。
在单调的春天和初夏,旅行和晚餐因大流行而暂时取消。走进乡村,走向户外,成为城市居民身心的归宿。
传统户外运动作为旅行的替代方式,在城市周边的山区和荒野中兴起,从爱好者群体扩展到普通大众。徒步、登山、骑行、攀岩、钓鱼、探险……有多少从未接触过户外、更别说露营野餐的“新人”,在这个春夏换上了运动服、买了装备?我穿好衣服,来到城市的荒野附近。
“现在不上,要等到什么时候?”
5月下旬,黄国松骑自行车去昌平慈悲谷,绕十三陵水库一圈。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练习攀爬,跑完100公里的路线后,我感到疼痛“绝望”。这是他第一次登山,因为他才骑行一个月。他不喜欢骑自行车。
对他来说,骑自行车只是健康的替代品。五月,健身房因隔离而关闭,所以我开始骑自行车来填补空闲时间并保持活跃。他的车是几年前朋友送给他的一辆二手车,是一辆入门级的美利达公路车,售价3000多元,全黑。
黄国松更喜欢在城市里夜骑,晚上9点后出门,开车绕城两个小时,行程40-50公里。有时从北鸟巢骑行到南四环沿中轴线直回,有时骑行到西边的新树河大桥远眺冰雪,有时骑自行车到东城胡同。我在北京从未见过如此不寻常的夜晚。王府井、三里屯等繁华商业区灯光昏暗,但商场前的广场却生机勃勃。人们玩得很开心,就像运动会一样。网、羽毛、跳绳、轮滑、滑板大家都挥汗如雨。“在太古里三里屯广场,每个人都穿着宽松的运动服,”他说,“与以前人们穿着整齐、大叔拿着相机拍街拍的日子不同,现在的景色已经完全变了。”
4月份以来,自行车在北京开始流行。当月,上海对整个疫情静态管理的打压,使其无法前行,通过网络传播,到了5月份,北京越来越多的社区被封锁。商场关门、演出取消、公园关门、游乐场关闭、餐饮暂停、学校停课……户外活动成了最后一个去处。清明期间黄国松骑着自行车下乡开车上山时,山上人不多,5月份再去时,自行车道上几乎堵车了。妙峰山、解塔寺、潭王路、黑山寨等往返不到100公里的线路上,不少“初学者”一脸兴奋。
这个春天,自行车界充满了“现在不骑,以后再骑”的情绪。你还是可以出去的。北京骑行爱好者林浩楠今年4月打破了骑行七年历史最高纪录,骑行近1700公里,爬坡超过10000米。4月以后,自行车团体停止了集体活动,坚持骑行上路的骑行者单独或以两到三人为一组出行。林浩南表示,两名骑行者见面时,会互相出示核酸证明,证明自己呈阴性。“如果现在不上,可能两天后突然就上不了了。那种强烈的未知感和无助感让你想出去,”他说。
读书和骑自行车是林浩南的两大爱好,在这个特殊时期都具有特殊的意义。他将阅读视为一种内部流放,而骑自行车则视为一种外部抵抗,后者更容易受到环境威胁。所以对他来说,此时骑行比读书更重要。
4月,从房山乘坐“柳市—红景”线的当晚,他和同事们顶着车灯,沿着松树岭漆黑的山路返回市区。当他在路边休息时,他的同伴突然让他抬头看。“你见过北斗七星吗?”我的同伴道。他说是的。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这位同伴,我很想请他和我一起去红景路。按照林的计划,“六石红井”本来是两天的行程,他也加入了这个疯狂的任务。“那天他在旅途中,一直在讲述所经过的村庄的历史变迁,以及太行山和燕山的形状有多么不同……”林浩南回忆道人,以及它带来的强大含义保持乐观,保持好奇,不要屈服于生活的疲劳和荒谬,或者至少更长时间地抵抗它。”
越来越多的日常活动被归类为“非必需”,城市和郊区一定程度的户外活动变得有必要取代旅行、聚会、晚餐和遛孩子。
“我认为户外活动只会变得更热,还有很多尚未开发出来的游玩方式,包括徒步旅行、登山、露营、骑自行车、越野跑、冲浪、潜水、帆船和桨板运动。皮划艇、攀岩、徒步旅行、滑雪等钓鱼、高尔夫、骑马……”一边说着这个“省”,李轩一边把新到的鱼竿拆开包装,放在货架上。他创办的JamesOutdoorLife户外品牌店就在北京。位于顺义市泉州保税区首都机场附近,主要销售露营用品,目前正在拓展登山、钓鱼等品类。6月1日下午,不到一小时的时间,一个小时,四批朋友来看装备,我找到了店面。
林红也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当天下午3点左右,她带着父母和儿子来到李轩的店里,他们一家今年开始采购露营装备,已经购买了“一室一厅”的帐篷、两张床垫、一张折叠桌椅。还有炉子……等等,花了将近一万块,这次我想找一把舒服点的椅子。这些物品几乎装满了她的SUV,但她还想买一台车载冰箱。
疫情发生后,她经常与农村朋友聚会,有时称其为“荒野聚会”。有时我们甚至在朋友的郊区院子里举办篝火晚会。她第一次购买装备时,随手预留了一些装备,后来在朋友的专业指导下,她换成了全套知名户外品牌,800元的桌子换成了1800元的桌子。她认为疫情过后露营不会停止,露营设备还会继续使用。“我们没有在郊区买房子。这个单位就像在郊区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客厅。想想就很划算了。”她笑着说。
夫妻俩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,都是大学教授,有定期出国旅游的习惯。日益富裕的经济条件导致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,而当疫情让这一切戛然而止,旅行计划也暂停时,乡村的户外活动几乎成了中产阶级生活的常态。
“表面上是露营、烧烤,但背后其实是家人朋友周末团聚的精神需求。同样,户外运动也体现了每个人探索世界的需求。”李玄总结道。“这些要求不是。停下来,它们是既定的。生活。”
户外活动的理由自由、独处、互动。
5月17日,蒋庆阳登顶云南省——哈巴雪山(海拔5396米),这是她的第一座雪山。她今年37岁,家住深圳,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高级人力资源职位,是一个9岁男孩的母亲。那天天气很不好,虽然导游说恶劣天气很少见,但她还是决定尝试一下。前两次雪山之行,她都停留在海拔5000米的高度,但这一次,她要突破极限。
2022年5月,张清阳装备攀登云南哈巴雪山。这是她开始攀登三年来首次成功登顶。提供照片/采访
最后几百米,队员们纷纷倒下,但决定胜负的因素是手套。手套又湿又冻,再这样下去,手就会被冻伤。江青阳除了标准的厚薄两双手套外,还戴上了特厚的手套,终于护送她到了山顶。与她同行的五个人中,她是唯一一个到达刻着“5396米”的木牌的人。
她去爬了几次山,可惜遇到了恶劣的天气,没能从雪山峰上看到传说中的“万年一见”的美景。但哪怕天上白雪皑皑,山上雾气缭绕,在她眼里也已经是值得一看的景象了。
张清阳拥有3年户外活动经验。2019年5月,我和领队第一次踏上雪山,当我们爬到海拔4800米时,一阵大风吹来,另一队有人滑倒了。沿着同一条路撤退。这座未完成的哈巴山峰是她户外事业的起点,从那时起她就一发不可收拾。疫情这两年,她一有机会就开始户外活动,每年五月、国庆、暑假,她都会进行户外活动,攀登四姑娘山第二峰、骑行环青海湖、攀岩、梅里北斜坡徒步。“每次我从户外回来,我都感觉自己重生了。”户外活动是她为自己发现的一种获取内在能量的新方式。动荡。需要持续的动力。“攀岩给了我动力。”
登山是最经典的户外运动之一。在18世纪的欧洲,通过探险和科学研究创造的登山、穿越和徒步旅行成为现代户外运动的开端。中国于1956年成立了国家登山队,肩负着攻占珠穆朗玛峰的国家使命,但民间登山队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,中国民间户外运动的历史也只有30年左右。
登山已成为深圳的一项热门运动。深圳周边没有海拔超过1000米的山峰,但疫情发生后,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将周边10座山峰包装在“深圳十峰”概念下,引发了大规模的登山热潮。小程序中时峰签到人数突破33万。深圳西船峰还有一支引人注目的童子军,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上山,有的公司还专门为孩子们举办登山活动。“双减”后,山体成为孩子们的新空间。张成阳9岁的儿子已经登上了十峰之巅,以前单独上课的朋友现在经常聚集在山上。
受疫情启发的户外运动热潮并非简单地源于人们对自然的突然热情,而是首先源于人们珍视的行动自由,然后源于被压抑的社会需求。疫情过后,人们突然发现城市生活的脆弱和狭隘,但广阔的原野却蕴藏着自由和活力。
2020年之前,江庆阳经常出国旅行,他认为旅行是由“由内而外”将所见所闻的风景内化的过程,而户外运动则是“由内而外”与身体较量的过程。两者对她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。在海外旅游停滞的时代,远离市中心的户外运动几乎取代了旅行。人们说,必须失去一些东西才能意识到它的价值,所以现在每次有机会离开我都会很珍惜。
对于骑行新手黄国松来说,骑行不仅是健身的替代品,也是出行的替代品。他是一位狂热的旅游爱好者,周末很少留在北京。疫情发生后,他花4999元购买了航空公司专门开发的“随心所欲飞”套餐,获得随时出门的机,飞往大部分地区,往返省份30至40个六个月内的次数。中国人。在过去的六个月里,他一直无法离开北京,但“我一直想出去,”他说。自行车只是无事可做时的最后手段。
疫情让生活陷入不确定和短暂的状态,让外出的小事变得重要,甚至是奢侈。这个时候,户外运动所带来的解放感就被戏剧性地放大了。
“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的狭小空间里。当你走出六环路时,你看到的是一个不像北京的北京。你面前的路是无尽的。这是一个自由的时刻。”林好曼晚上回到高楼时说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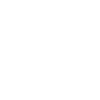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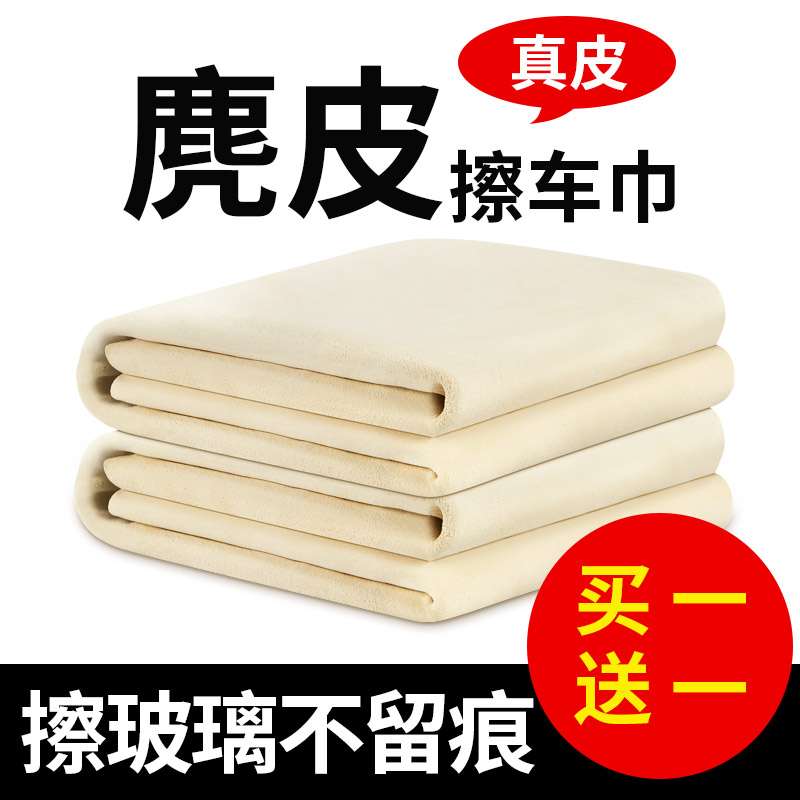

No Comment